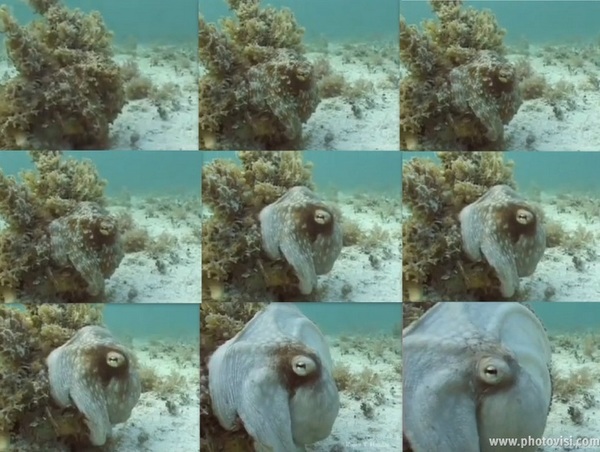即將失業的麻省理工學院校友
1975 年的某個冬天,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生化教授博耶(Herbert Boyer)莫名其妙地接到一通自稱是在舊金山創投資公司 KPVC(Kleiner Perkins Venture Capital)工作之史旺森(Robert “Bob" Swanson)打來的電話,希望能與他會面談談;忙於工作的博耶,心不甘情不願地勉強答應在一個周五下午給史旺森 10 分鐘的時間。隔年元月 17 日,史旺森如約地拜訪波以耳的實驗室,沒想到原本 10 分鐘的會談,從實驗室到酒吧,竟變成了三個小時;而在幾瓶啤酒下肚後,更沒想到之後一個革命性的生物科技產業就此誕生了!
- 編按:KPVC 後加入了另外兩位合夥人,改稱為 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中文譯為「凱鵬華盈」。
![]()
史旺生。生化教授博耶在史旺生的說服下,一個革命性的生物科技產業就此誕生了!圖/By Chemical Heritage Foundation, CC BY-SA 3.0, wikimedia commons
史旺森 1947 年出生,1970 年在麻省理工學院同時取得化學學士及商業管理碩士學位。他畢業後即加入花旗銀行創投部門,卻經歷了一連串投資失敗。在他灰心想換工作時,曾與他合作過一次的克萊納(Eugene Kleiner)因他思想敏銳、做事效率高,而於 1974 年年底把他拉進 KPVC。
帕金斯(Thomas Perkins)回憶謂:史旺森雖然做了幾件案子,但均不是非常成功,因此連克萊納也漸漸對他不滿。是否因此之故,史旺森也不清楚,但克萊納及帕金斯在 1975 年年底告訴他説:「唉,我們很想只有我們兩人工作。……但在你知道要做什麼之前,你可以繼續保留辦公桌及電話。」這顯然暗示他明年就沒有工作了!
不過史旺森是個科普及科幻迷,當他看到基因改造及基因工程等報導時,立即意識到了這將完全改變人們對基因與遺傳之思路。因此史旺森告訴 KPVC,他將看看生物科技方面有什麼可以做的……。
青蛙王子
1972 年,史丹佛大學生化教授伯格(Paul Berg)成功將 λ 噬菌體(感染大腸菌)的一段 DNA,接連到 SV40 濾過性病毒(感染猴子)的 DNA 上,闡釋了「基因改造」的可行性(他因之獲得了 1980 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分得一半的獎金)。
他原想讓這由兩種不同物種基因體組成的 SV40 去感染細胞,複製其混種 DNA 及蛋白質;但突然警覺到:雖然原來之 SV40 對人體無害,但改種過的過濾過性病毒,萬一變成無法控制、對人體有害的傳染病呢?他因此召集同行,於 1973 年元月及 1975 年二月在加州太平洋岸邊的 Asilomar,討論基因改造可能引起的倫理道德及科學家責任等問題。
博耶就是在第二次的 Asilomar 會議裡,碰到了另一位由史丹佛大學來的生化教授科恩(Stanley Cohen);兩人在沙灘上的深夜長談後,發現他們的研究互補——博耶是基因限制酶(restriction enzyme)專家,而科恩則善長於細菌質體(plasmid ,註 5)的操作——因此兩人很自然地決定合作。
1974 年 5 月,他們成功地完成「青蛙王子」的實驗:將青蛙的部份基因導入大腸桿菌的質體內,讓它隨細菌大量繁殖(大腸桿菌每 20 分鐘複製一次)。當同事問科恩怎麼知道青蛙的基因被「表現」出來時,他總是開玩笑地説:與細菌親嘴,看它是否會變成王子就知道了!
基因泰克公司
如果放進質體的不是青蛙的基因,而是製造胰島素的基因呢?
史旺森似乎毫無困難地説服了博耶:兩人決定各出 500 美元,於 1976 年 4 月 7 月在舊金山正式登記成立 Genentech——由 Genetic Engineering Technology 縮寫而成,中文譯成「基因泰克」。史旺森回憶説:「我不支薪,靠每月 410 美元的失業保險金過日子;我與人同租一間 500 美元的公寓,月付 110 美元租一部 Datsun 240Z 的汽車;其它的就是花生醬三明治,以及偶爾看個電影。我當時雖有些存款,但不多。」
代表基因泰克的洛杉磯律師齊理(Thomas Kiley)——1980 年加入該公司,後來當了法律副總——到舊金山出差時,也只能睡在史旺森那「不起眼」公寓中的沙發。6 月,史旺森寫了一份 8 頁的計畫書,希望 KPVC 能投資 50 萬美元;KPVC 快速地審查後,認為「投機性太大」,因此只答應撥款 10 萬美元相助。1977 年 2 月第二次集資 85 萬美元時,KPVC又投入了 10 萬。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那裡去找製造胰島素的基因呢?人類的胰島素基因在第 12 號的染色體上,可是要分離出來並不簡單,因此博耶決定自己合成。
- 哈佛大學的吉伯特(Walter Gilbert,註 6)及桑格(還記得他吧?)於 1977 年因發展出快速決定 DNA 核酸順序的方法,而合得 1980 年另一半的諾貝爾醫學獎
由於倫理道德的考量,將不同物種 DNA 重新組合的「重組 DNA」(recombinant DNA)技術在兩次阿西洛馬會議(Asilomar conference)後,慢慢受到許多限制(例如政府補助)。因此博耶決定研發人工合成胰島素,這「不經意」的決定,事實上可能「救」了基因泰克公司,使它能在「劇烈競爭」下脫穎而出:吉伯特及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另一團隊古徳曼(Howard Goodman)和盧特(William Rutter,註 7)也均在研究透過「基因改造」(使用「自然基因」)來製造胰島素。
生長抑制素基因
博耶不是有機化學家,因此找了洛杉磯附近之「希望之城國家醫學中心」(City of Hope National Medical Center) 的兩位 DNA 合成專家板倉啓壹(Keiichi Itakura)及里格斯(Arthur Riggs)幫助。可是胰島素具有 51 個胺基酸,似乎太複雜了點;為了能快速確定他的想法是否行得通,博耶同意兩位專家的建議,並説服「要幹就幹實際的」的史旺森,決定先合成同樣也是胰臟分泌、卻只具 14 個胺基酸的生長抑制素(somatostatin)基因。
在博耶著急地催促下,板倉啓壹及里格斯兩人果然不失眾望,在 1977 年 6 月邀博耶及史旺森南下一齊觀察最後的勝利產物:不幸地,他們並沒有偵測到大腸桿菌製造出來的生長激素抑制素!這對史旺森是個相當大的打擊,隔天早上他因急性消化不良,被送到急診室去。史旺森回憶説:「我看到我整個職業生涯付之流水。細菌(大腸桿菌)照理應製造出蛋白質,但我們一點都沒看到!」
為什麼失敗呢?與細菌為伍多年的博耶猜想:細菌可能以為生長激素抑制素是外來的入侵者而將它「吃掉」,因此他建議在生長激素抑制素基因上,加掛一些細菌本身的基因(基因改造)來誤導細菌,以爲它們在製造自己的蛋白質,然後將細菌的蛋白質部份切掉,即可得到生長激素抑制素。這一策略果然奏效,三個月後,在史旺森閉目不敢視的緊張局勢下,他們終於偵測到細菌製造出來的蛋白質,板倉啓壹轉身指著報表告訴史旺森說:「生長激素抑制素在此!」
1977 年 12 月 2 日,各地新聞報導了類似《華爾街日報》所刊登之:
科學家首次透過基因操作製出了有用的蛋白質……這在醫藥研究上是一非常巨大的突破,它意味著科學家可能藉細菌製造出便宜的合成荷爾蒙。事實上正如美國科學促進學會(AAAS)所言,此一突破將導致「生物學上的革命」。
7 天後,以板倉啓壹為首的研究論文出現在 AAAS 所出版之 Science 期刊上。
南舊金山
這一令人鼓舞的結果讓史旺森決定基因泰克該有自己的實驗室了。在房地產朋友的推薦下,他終於決定在南舊金山的一片倉庫處定居下來。物以類聚,後來許多生化科技公司也相繼設廠於此城,使它意外地成為美國生化科技中心。如果讀者有機會拜訪該城(在舊金山機場附近),你將可在生化科技區的進口處看到「南舊金山/生化科技的誕生地」的標誌。
除此之外,史旺森也正式開始聘請一些自己的科學家:例如克萊德(Dennis Kleid)及他的博士後研究員哥德爾(David Goeddel)。在挖角克萊德時,克萊德謂如果不同時也雇用哥德爾的話,那他也不會離開史丹佛研究所(不屬於史丹佛大學的一個非營利研究中心)。克萊德果然慧眼識英雄:哥德爾於 1978 年 3 月加入基因泰克公司後,該公司所有的早期產品幾乎全是他(基因)「複製」出來的;他可以説是基因泰克公司之所以有今日之地位的最大功臣,為一生物科技及分子生物界的傳奇性人物。
人造胰島素
成功製出生長激素抑制素蛋白質非但沒有讓他們慢下來,事實上反而讓他們更加快了腳步。
1978 年 5 月,他們成功地在細菌內「合成」胰島素的 A 及 B 鏈;7 月純化了那兩條蛋白質;8 月初去蕪存菁地將細菌的蛋白質剪掉;8 月 21 日的深夜,哥德爾——不錯,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傳奇性人物——成功地在試管內將 A、B 兩鏈連在一起,造出了第一個以生物科技「合成」的人造胰島素!由 12 人組成的全世界第一家生物技術公司,竟然以小搏大,贏了這場競賽。
克萊德回憶說:「我們到達終點時相當精疲力盡,過一段時間後我們才真正體會到贏了這場競賽。」
禮來製藥公司臨床試驗顯示了,這個人造迪道速不但同樣具人類胰島素的效果,且不會像動物胰島素一樣讓某些人過敏!四天後,禮來就先付 50 萬美元的(知識產權)授權費,與基因泰克公司簽定了 20 年的研發合約。這時間事實上來得正好:因為當克萊德加入基因泰克公司、去參觀禮來之一製造胰島素工廠時,他發現整列的火車載滿了冷凍的豬、牛胰臟,在那裡等著入庫。禮來每年需要五千萬頭的豬、牛才能勉強供應胃口越來越大的胰島素市場;因此如果基因泰克公司不能即時提供所需,禮來很可能去找其對手。
但克萊德認為他們剛發展出來的效率太低,將不足應付需求。當他將此想法告訴史旺森時,史旺森回説:「我不想聽到『不可能』這個詞,告訴我你要怎麼樣才能做到。」1980 年,基因泰克公司的科學家們終於找到了一強大的控制基因,能在適當時刻「告訴」質體大量製造胰島素,使產能激增了 50 倍!
哥德爾成功地在試管內將 A、B 兩鏈連在一起的兩個禮拜後,1978 年 9 月, 基因泰克公司申請「以基因改造讓微生物製造任何蛋白質」的專利。有觀察家認為這等於承認基因泰克公司發明了(所有)基因改造的微生物!
可是生命是自然界的現象,能專利嗎?1980 年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GE)的科學家查克拉巴蒂(Ananda Chakrabarty)發展出一種可以分解原油的細菌,申請專利時卻被美國專利局以「就一般所瞭解,生物不是可專利的題材」駁回;經上訴(基因泰克的齊理也曾出庭為奇異公司辯護),美國最高法院最後以 5 比 4 裁決奇異公司獲勝。
最後美國專利局於 1981 年 3 月 31 日正式核准了該項專利,為基因泰克公司預舖了通往康富的大道。1982 年 10 月 26 日美國專利局批准了基因泰克公司的第一個(也是科技歷史上最賺錢的)專利。1983 年美國藥物管理局批准了禮來用基因改造所製造出來的胰島素(第一個基因工程藥物)上市。雖然從動物胰臟中提煉的舊法成本較低,但因各種(包括心理在內之)因素,用基因改造所製造出來的胰島素現今幾乎已全取代了所有的動物胰島素。據估計,全世界胰島素的市場將從 2015 年的 270 億美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436 億美元。
生物科技產業
基因泰克公司於 1980 年 10 月 4 日上市,為全世界第一個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在一小時內從開價每股 35 元,跳到 88 元,最後以 71.25 元收盤,共集資 3500 萬元,為最成功的「首次公開募股」(華爾街日報謂「最令人注目之一的首次市場亮相」)。2009 年瑞士羅氏大藥廠(Roche)以 468 億美元收購所有它未擁有的基因泰克公司股票(意即基因泰克公司已不再是一獨立的上市公司)。
史旺森於 1999 年 12 月因腦癌而英年(52 歲)早逝。他被認為是生物科技革命的先知與先鋒;在 1998 年 12 月出版之 1,000 Years, 1,000 People: Ranking the Men and Women Who Shaped the Millennium 一書內,以他是「生物科技革命的先鋒」排名第 612 位。
麻省理工學院校長魏司特(Charles Vest)説:「麻省理工學院很榮幸有史旺森這樣的校友。……他是典型的美國企業家,不只創辦了一個公司,而是整個產業——一個創造財富及工作、但更重要地改進了健康和生活品質的產業。」
後記:台灣生物技術感言
1979 年五月,行政院通過「科學技術發展方案」,將能源、材料、資訊、與生產自動化列為四大重點科技。然後就在美國生物科技產業剛起步不久的 1982 年修訂,增列生物技術、光電科技、食品科技、及肝炎防治等四項,成為八大重點科技計畫。台灣一直是全球 B 型肝炎的高度感染區之一,因此將發展 B 型肝炎疫苗做為台灣八大重點科技計畫應是顯而易見、理所當然的正確決定。
那時美國的生物技術剛起步不久,我們不是正好可以趕上了時代,一石兩鳥地加入行列,研發以生物技術來製造第二代的 B 型肝炎疫苗、來取代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剛在 1981 年批准的第一代 B 型肝炎疫苗(由病患者血液中萃取出來的表面抗原蛋白)嗎?這事實上不正是前面胰島素發展之歷史借鏡嗎?但「不幸」的是,我們還是決定取捷徑,以「技術轉移」來發展重點科技:於 1984 年由行政院開發基金管理委員會、交通銀行、中央投資公司、及生技中心共同投資,成立一家技轉疫苗工廠「保生公司」!
1981 年,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及柏克萊分校的三位教授盧特(William Rutter,我們在故事中曾碰到他),Edward Penhoet 及 Pablo DT Valenzuela 合創了 Chiron 公司,成功地於 1986 年發展出第一個透過酵母菌基因改造製造出來之 B 型肝炎疫苗。臺灣的肝炎防治重點科技計畫只是晚了一年提出,但我們有全國的經濟與人才做後盾,怎麼竟然連試一下自行研發都不敢呢?
筆者很想説或許是我們缺乏人才,但每思及 2015 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屠呦呦的一生遭遇,筆者總覺得問題比此更深遠:缺乏自信[註 8]、崇洋[註 9]、不患寡而患不均(決策容易,人人有獎,但培養不出明星教授)、政治介入、官大學問大[註 10]、官商勾結、先撈一筆再說、……等心態?
「保生公司」因種種因素,於 1995 年關門大吉。肝炎防治的重點科技連個「技術轉移」都無法實現,能不悲嗎?而生物技術的重點科技,也因為五年前的「宇昌案」及去年的「浩鼎案」鬧得滿城風雨,看來我們終將還是未趕上「生物技術」的「先進國家列車」。機會像青春一樣,一蹤即逝,一去永不回,惜哉!
- 筆者謹在此謝謝國家衛生研究院生技與藥物研究所副所長謝興邦博士,不斷地提供台灣政、學、經、及生物醫學重大消息,聊解異國遊子思鄉之渴。
註解
- 5. Plasmid 中文譯成「質體」,實讓人不知所云。它是細菌染色體之外的小圈形雙螺旋 DNA 分子,可像染色體一樣自行複製,也帶基因(大部份是為了生存),很容易取得、注入、或在(不同)細菌間互換,因此成了生物科技的「寵物」:做為其它基因的攜帶體。
- 6. 1978 年合創 Biogen,最成功的藥物是基因改蛋白質 α 干擾素(α‑interfero)。
- 7. 1981 年合創 Chiron,發展第一個透過酵母菌基因改造製出之疫苗(B 型肝炎)。
- 8. 不管做什麼,一定都會有對手的。如故事中所述,基因泰克初創時讓他們寢食難安的兩大對手是也在做同樣研究的哈佛大學及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兩個基因工程萌芽的聖地。1978 年夏天,聽説吉伯特即將宣佈成功地分離出人類胰島素基因時,史旺森又差點被送進醫院——幸好因污染的關係,事實上吉伯特所分離出來的只是他們用來做實驗的青蛙胰島素基因。
- 9. 外來的和尚才會唸經:賴昭正文「為何台積電不能」,科學月刊,2014 年 10 月號。
- 10. 2003 年,19 歲史丹佛大學輟學生創立之 Theranos,宣稱只用一滴血就可做許多分析與測驗。曾紅極一時,董事會裡曾大都是政界名人,創辦人於 2015 年被福布斯(Forbes)雜誌列為美國最富有的白手起家女士,但突然問題一大堆,2016 年其估計財產由 2015 年的 45 億元驟降至零。
The post 人造胰島素開啟生技產業——胰島素與生技產業的誕生(下) appeared first on PanSci 泛科學.